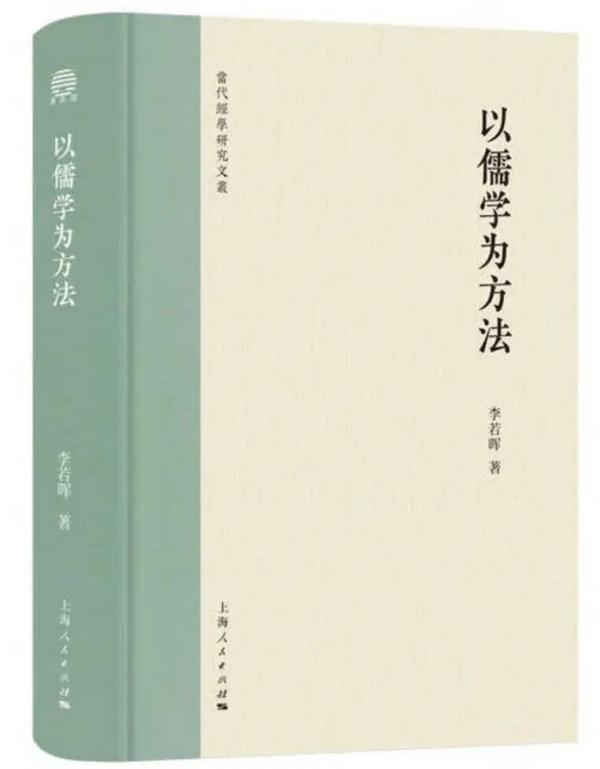“通志堂·當(dāng)代經(jīng)學(xué)研究文叢”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25年9月
【內(nèi)容簡介】
本書對于儒學(xué)的研究,重在探索在中國研究中建構(gòu)自身的方法論。本書從社會結(jié)構(gòu)、政治制度、倫理道德、哲學(xué)思想四個維度出發(fā),試圖扭轉(zhuǎn)當(dāng)前儒學(xué)研究中的一些不良傾向,努力重建儒學(xué)的整全面相。作者指出,社會行為的公共性即為政治,包括政治哲學(xué)與政治制度;社會行為的個體性即為道德,包括道德哲學(xué)與道德范式。道德和政治構(gòu)成了一定人群的基本行為模式。而對行為模式予以解釋,對道德提供論證的是哲學(xué)思想。何以能夠以此行為模式行事的根基,則是與倫理道德和政治制度相適應(yīng)的社會形態(tài)。
本書對儒學(xué)的四重結(jié)構(gòu)進行了系統(tǒng)的剖析,并由此深入論述了儒學(xué)在中國古今之變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發(fā)揮出這一作用的條件。由此,作者強調(diào),儒學(xué)不是研究的“客觀”的對象,而成為理解中國、面向未來的研究方法。
【作者簡介】
李若暉,中國人民大學(xué)國學(xué)院教授、經(jīng)學(xué)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中國哲學(xué)、中國德性政治史、中國古典語言文獻研究。著有《老子集注匯考》《不喪斯文:周秦之變德性政治論微》《久曠大儀:漢代儒學(xué)政制研究》等。
【目錄】
序 儒學(xué)與中國的方法透鏡/任劍濤1
緒論 儒學(xué):由對象到方法1
第一節(jié)儒學(xué)的現(xiàn)代境遇1
第二節(jié)思想與制度7
第三節(jié)儒學(xué)作為方法13
第一章 儒學(xué)的制度之維及中國哲學(xué)之成立21
第一節(jié)“中國哲學(xué)”作為傳統(tǒng)思想之棺槨23
第二節(jié)“創(chuàng)造歷史”與創(chuàng)造未來35
第三節(jié)文之得喪任諸己51
第四節(jié)“漢家制度”與“治出于二”57
第二章 第一維度:社會結(jié)構(gòu)75
第一節(jié)家內(nèi)結(jié)構(gòu)75
第二節(jié)喪服與昭穆89
第三章 第二維度:政治制度118
第一節(jié)古代中國地方力量“自下而上”的運作:重論
費孝通“雙軌政治”119
第二節(jié)寓封建于郡縣:論費孝通“雙軌政治”的歷史
真實142
第四章 第三維度:倫理道德166
第一節(jié)“倫”的語義與哲理166
第二節(jié)“無父無君”之孝:曾元養(yǎng)曾子之哲學(xué)分析182
第五章 第四維度:哲學(xué)思想193
第一節(jié)論正常之惡:郭店竹書《魯穆公問子思》的哲學(xué)
分析194
第二節(jié)人何以能質(zhì)疑鬼神:上博竹書《鬼神之明》中的
人之知202
第三節(jié)論非暴力被動強制:古公亶父避狄之哲學(xué)
分析212
第六章 儒學(xué):真實認識中國231
第一節(jié)重返費孝通思想的歷史視野231
第二節(jié)賤籍與身份社會245
第三節(jié)中國古代對于君主專制的批判252
第七章 余論:儒學(xué)與中華文明之未來279
第一節(jié)儒學(xué)必須補課279
第二節(jié)儒學(xué)與血緣282
第三節(jié)皮錫瑞與“王朝經(jīng)學(xué)”之終結(jié)287
參考文獻294
后記316
【序】
儒學(xué)與中國的方法透鏡
任劍濤
關(guān)注儒學(xué)研究動態(tài)的朋友們一定會發(fā)現(xiàn),近期的儒學(xué)研究呈現(xiàn)出突破性的態(tài)勢。由于儒學(xué)研究在政治上的脫敏,解除了儒學(xué)研究就是為“封建意識形態(tài)”招魂的禁錮,這讓儒學(xué)研究逐漸釋放出活力,儒學(xué)研究的多元化局面就此浮現(xiàn)。多元化的儒學(xué)研究不是無主題變奏,而是圍繞一個主軸展開的,那就是儒學(xué)的價值與知識。圍繞這一主軸展開的儒學(xué)價值與知識論述,豐富多彩,呈現(xiàn)為大不相同的研究取向,形成了令人贊嘆的儒學(xué)研究繁榮局面:在價值上,有堅執(zhí)儒家價值的,也有拒斥儒家價值的。在兩個極點之間,對儒家價值的認取與排斥,在不同光譜上呈現(xiàn)出來,體現(xiàn)出儒學(xué)在現(xiàn)代價值建構(gòu)上的資源多樣性。在知識上,儒家整全性體系的各個構(gòu)成側(cè)面,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展示,讓儒學(xué)的知識面相豐滿地呈現(xiàn)在人們面前。儒學(xué)知識面相的現(xiàn)代重構(gòu),不惟幫助人們理解儒學(xué)的傳統(tǒng)面相,而且也有助于人們認識到儒學(xué)是現(xiàn)代人文與社科知識建構(gòu)的寶貴資源。借助于構(gòu)成中國傳統(tǒng)核心支撐系統(tǒng)的儒學(xué),人們不僅更加深刻地認識了傳統(tǒng)中國,也愈加理解建構(gòu)現(xiàn)代中國的儒學(xué)資源之不可或缺。這是一個儒學(xué)研究的可期局面:以儒學(xué)為中介,清楚認識傳統(tǒng)中國;以儒學(xué)為媒體,清晰刻畫現(xiàn)代中國。
李若暉撰著的《以儒學(xué)為方法》,就是在儒學(xué)呈顯出繁榮局面中提供給讀者的一部精心之作。他的這部著作,是一本儒學(xué)專題論著。專題論著與專著有所區(qū)別。專著是圍繞一個主題,從多方面展開集中性論述;專題論著是圍繞多個主題,發(fā)散性地討論問題。但不是說專題論著的多個主題之間就沒有聯(lián)系,而是說它的主題間關(guān)系有可能達到更高層次的論域。這一論域投射在各主題中間,向人們展現(xiàn)出更為宏闊的理論空間。可以說,儒學(xué)研究的專題論著,一般會以論述的高度與廣度,顯示出與儒學(xué)專著的深度取向大不相同的特點。
若暉的這部著作,以儒學(xué)為方法,不僅以此呈現(xiàn)出與儒學(xué)諸多研究者不同的研究進路,而且因為他的論述視角、主題擇取、資源借取、意圖確定等方面所具有的特點,而顯出與流行的儒學(xué)作品不一樣的獨特價值。這正是說他的這部著作是一部精心之作的重要理由:這里的精心,不僅是指若暉用心于儒學(xué)研究突破口的尋找,而且是指他在儒學(xué)流行見解中精思明辨以出新意,更是指他在儒學(xué)研究的眾聲喧嘩中冷靜而理性地進行絲絲入扣的分析。他舉起入微觀察儒學(xué)與中國的方法透鏡,將儒學(xué)與中國互動的豐富內(nèi)涵展現(xiàn)出來。
這確立起他這部著作幾方面的重要價值:
首先,他確立的“以儒學(xué)為方法”研究進路,有著扭轉(zhuǎn)長期以來形成、以至于成為定勢的“以儒學(xué)為對象”的研究局面。若暉自己明確意識到“中國哲學(xué)”界所展示的儒學(xué)研究進路的多樣性,但這類研究,大多將儒學(xué)安頓在研究“對象”的位置上,即便是表達出對儒學(xué)具有信仰的研究者,也是把它視為信仰的對象。將儒學(xué)作為對象,確實可以凸顯儒學(xué)的一些重要面相,因為對象化的審視可以將之作為信仰、信念與知識等不同表達所資借的源泉。但將儒學(xué)對象化之后,表達價值信仰者會對儒學(xué)進行理想化的提純,進行知識重述者會將儒學(xué)納入自己的背景性既定知識框架之中。這樣一來,儒學(xué)“自身”的面目反而難以呈現(xiàn)出來。尤其是近代以來將儒學(xué)哲學(xué)化的種種嘗試,以及由此形成的“儒家哲學(xué)”,實在是既未能揭示儒學(xué)的真實面貌,也未能凸顯儒學(xué)的現(xiàn)代出路。這是一種必須解除的雙重遮蔽。若暉在斷言“中國哲學(xué)”是傳統(tǒng)思想棺槨的基礎(chǔ)上,明確表示需要將對象化的儒學(xué)研究轉(zhuǎn)換為以儒學(xué)為方法的新范式:這是一種旨在將儒學(xué)思想與中國制度內(nèi)在勾連起來觀察與分析的新進路,他的兩個論述宗旨由此展現(xiàn)出來:一是“儒學(xué)是把握和理解中國的主要方法”,二是“儒學(xué)作為方法,也是把握和理解儒學(xué)自身的重要方法”。這是一種儒學(xué)與中國雙向限定的方法理念,它試圖實現(xiàn)兩個超越:一是超越思想與制度脫節(jié)的儒學(xué)研究,二是超越提純?nèi)鍖W(xué)與真實中國的脫節(jié)。進而在兩者關(guān)聯(lián)互動的基礎(chǔ)上,解釋真實的儒家,揭橥真實的中國。他的方法儒學(xué)主軸于此呈現(xiàn):“我們不應(yīng)‘創(chuàng)造歷史’,而應(yīng)創(chuàng)造未來”。
其次,他對儒學(xué)的四重結(jié)構(gòu)進行了系統(tǒng)的剖析,并由此深入論述了儒學(xué)在中國古今之變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發(fā)揮出這一作用的條件。在具體從四重結(jié)構(gòu)分析儒學(xué)與中國之前,若暉確立了論述儒學(xué)與中國的三個基本結(jié)論:“其一,大格局,中華古典政制是道德與政治的合一,是德與位的合一,承載德的是家族,承載位的是君權(quán),而中華政制的內(nèi)在矛盾即是家族與君權(quán)的矛盾,家族盛則有德無治,君權(quán)盛則有治無德;其二,這一格局由三圣王所奠定,堯奠定了天人合一傳統(tǒng),舜奠定了孝治合一傳統(tǒng),禹奠定了位德合一傳統(tǒng);其三,變局是,周代以后,無法再實現(xiàn)以位定德,孔孟將其更改為以德定位,家族承載道德,與君權(quán)相對抗,形成士族門閥制度,隋唐用科舉解決豪族問題,北宋解決藩鎮(zhèn)問題。同時,在社會層面上,理學(xué)家建立縣下家族,承載道德,但是縣下家族不再成為國家層面的政治力量,君權(quán)失去了制衡,從而權(quán)力過盛。”在漢家劃分出“治出于一”與“治出于二”的界限,即治理理想與治理現(xiàn)實的統(tǒng)合與分離的界限以后,如何呈現(xiàn)國家治理的理想與現(xiàn)實的分離,便成為全面展示儒學(xué)與中國真實圖像的一個重要準(zhǔn)則。
這為他具體分析儒學(xué)與中國的社會結(jié)構(gòu)、政治制度、倫理道德與哲學(xué)思想確立了基本路向。分別地看,在社會結(jié)構(gòu)維度,若暉恰中肯綮地指出,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結(jié)構(gòu)確實是建立在家庭的基礎(chǔ)上,但社會結(jié)構(gòu)并不是家內(nèi)結(jié)構(gòu)的直接挪移。在家內(nèi)結(jié)構(gòu)中,父子之間盡管被世代規(guī)則所限,但一個人為了個人利益卻可以犧牲家的共同利益;在社會結(jié)構(gòu)上,有家的結(jié)構(gòu)衍生出來的昭穆制與五服制,以其世代差異與尊卑區(qū)分遵循著兩個不同的邏輯。那種簡單地以五服制看待社會圈層擴展、甚至是國際關(guān)系的思路,其實導(dǎo)出的不是一種平等關(guān)系。因為五服有著“親盡”的預(yù)設(shè)邏輯,而不像昭穆制那樣序時代,更有利于圈層擴展。因此,將家單純看作善性中國的基礎(chǔ),便不成立。
在政治制度維度,若暉認同從中國傳統(tǒng)政治的雙軌政治,也就是“從上到下”與“從下到上”的兩軌來理解中國傳統(tǒng)政治。但他強調(diào)指出,與一般都重視前一軌道的研究不同,他更重視后一軌道的再現(xiàn)。據(jù)此他主要落墨在東漢以后到隋唐這一段歷史上,花費大功夫重述了中古中國,也就是三國魏晉南北朝的中國政治史,鮮明刻畫出與中國大一統(tǒng)政治完全不同的地方政治勢力坐大的歷史,據(jù)此指出了中國傳統(tǒng)政治結(jié)構(gòu)皇權(quán)至上的鮮明對比面。這就促使人們意識到君權(quán)與族權(quán)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以及這樣的關(guān)系對人們認識整個中國傳統(tǒng)政治結(jié)構(gòu)所具有的獨特意義。這與前引他確認的三個基本結(jié)論吻合起來。至于中國傳統(tǒng)政治機制,或者說中國傳統(tǒng)政體的封建制與郡縣制關(guān)系,他經(jīng)過分析后強調(diào)顧炎武所說的“寓封建于郡縣之中”的中國混合政體,對理解中國古代政制所具有的確當(dāng)性。
在倫理道德維度,若暉依循前賢,將倫理學(xué)說之“言”,倫理認識之“知”,倫理行為之行結(jié)合起來考察。由此得出結(jié)論:以第一方面言,儒家人倫是人與人的相互(平等)關(guān)系,而不是三綱那樣的傾斜性關(guān)系;就第二方面講,儒家在親親與尊尊之間實際上表現(xiàn)出某種張力,而不應(yīng)等量齊觀;拿第三方面論,從前述的兩個問題可以推導(dǎo)出,儒家的倫理行為邏輯,不是高位或優(yōu)勢一方對低位或劣勢一方的單純支配,在倫理行為的實際發(fā)生過程中,行為關(guān)聯(lián)的雙方或多方實際是處在一種微妙的互動狀態(tài)之中。
在儒家哲學(xué)維度,若暉枚舉性地考察了儒家傳統(tǒng)中論及君臣關(guān)系言辭的秩序意涵,對臣下“極稱”君之惡進行了很有新意的分析,指出臣下忠君并不是忠于君王一人,而是忠于君王的道德。因此君臣關(guān)系不是單向制約的關(guān)系,而是雙向影響的關(guān)系。在分析鬼神之明與人之聰明關(guān)系的論述中,他指出墨家認定后者無法質(zhì)疑前者之誤,因此倡導(dǎo)一種儒家式的人質(zhì)疑鬼神之明的權(quán)利。從而以人能夠知曉賞罰的規(guī)則與適當(dāng)采取賞罰行為,而有理采取一種贊賞鬼神同時質(zhì)疑之的態(tài)度。他還以古公亶父避狄事件,從哲學(xué)上分析了保民而王的儒家政治原則,指出了毫不妥協(xié)的戰(zhàn)爭對壘與避戰(zhàn)保民的妥協(xié)選擇相比而言,后者所具有的特殊政治價值。
若暉這四個維度的案例性分析,是一種選擇性分析,而不是一種整全性概括。這似乎給人以方法錯位的感覺:既然試圖以儒學(xué)為方法解剖中國,這個整全性預(yù)設(shè),難道可以在案例分析中確證?不是應(yīng)當(dāng)在整體性概括中印證總體性結(jié)論嗎?這是一個有益的質(zhì)疑,但并不足以顛覆若暉的方法預(yù)設(shè)。原因很簡單,從典型個例出發(fā)論證整體狀態(tài),在方法上是可以成立的。這種論證,與整體描述以認知總體狀態(tài)具有同等價值。而且,如將若暉的四個方面整合起來看,確實具有幫助人們認識儒學(xué)與中國總體情形的作用。這比之于以往的單方面突進,即大多在其中某一方面展開來講,尤其是相比于僅僅從“中國哲學(xué)”的角度所做出的論證,具有一種相互印證或互相支撐的效用。
再次,他對儒學(xué)思想與制度的具體解析,秉持一種優(yōu)劣兼及的理性中正態(tài)度,因此勝意迭出。而且,他對儒學(xué)研究諸家的見解進行了深入辨析,有著糾正儒學(xué)流行見解的作用,這也使得他這部著作呈現(xiàn)出鮮明的論辯特色。若暉這部著作對儒學(xué)的論述,不僅在總體規(guī)劃上不同于坊間唯求儒學(xué)提純,將之視為毫無缺陷的完備體系;而且也不同于一味拒斥儒學(xué),將之批判得體無完膚的那些作品。前述他對儒學(xué)四個構(gòu)成面的重大主題分析,已經(jīng)顯現(xiàn)出這一特點。如果要舉出一個更具有典型意義的例證,便體現(xiàn)在他對中國傳統(tǒng)專制主義政制的辨析上。人們一般認為,中國古代政制屬于專制主義政治,但若暉專門分析了中國古代對專制主義政治批判的例證,這就發(fā)揮出糾正人們一面倒認定中國古代屬于專制主義政治定見的積極作用。他在四個維度的選定主題分析中,對社會學(xué)資源的高度重視,讓他在辨析中呈現(xiàn)出從中國傳統(tǒng)社會結(jié)構(gòu)透入儒學(xué)與中國互動態(tài)勢的最深層次,從而對費孝通“差序格局”與“雙軌政治”、潘光旦“倫”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學(xué)分析有足夠的印證和明顯的推進。它對歷史學(xué)界相關(guān)陳述的引入與辨析,尤其是對“中國哲學(xué)”界的相關(guān)知識闡釋所作的評論,深具啟人思考的作用。顯然,若暉“以儒學(xué)為方法”的研究進路,重視社會學(xué)知識傳統(tǒng)的分量勝于中國哲學(xué)的相關(guān)積累,看重制度層面對理解中國傳統(tǒng)的意義重于價值觀念維度的守持,推崇社會視角的傳統(tǒng)理解勝過對抽象觀念的推導(dǎo)。這是他以明確的方法優(yōu)先意識顯現(xiàn)出來的論述特點。尤其是他對中國傳統(tǒng)文獻學(xué)的修養(yǎng),幫助他在人們不經(jīng)意或經(jīng)意卻理解不到位的文獻中導(dǎo)出新見。這是他足以在昭穆制與五服制之間展示儒家親親原則外推及其限度和效度的解釋創(chuàng)新的知識積累優(yōu)勢,也是他在出入于費孝通、潘光旦的中國傳統(tǒng)之社會學(xué)分析而有所推進的知識儲備長處。
最后,若暉“以儒學(xué)為方法”對儒學(xué)與中國的論述,主要著眼點確實是在重釋傳統(tǒng)儒學(xué)與傳統(tǒng)中國,以及兩者互動的狀態(tài)。但他并不限于對真實傳統(tǒng)的還原。前已提及,他明確反對“創(chuàng)造歷史”,鮮明主張“創(chuàng)造未來”。這就必然表現(xiàn)出從歷史通向未來的論述旨趣。這里有個相關(guān)論述機制,即在中國傳統(tǒng)視角需要凸顯“真實中國”,這就是若暉所說的關(guān)聯(lián)性地解釋中國傳統(tǒng)的“思想與制度”所指向的那個中國。這個中國,在他看來,是以西方哲學(xué)為典范的“中國哲學(xué)”所無力揭示出來的:它需要重啟解釋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現(xiàn)代中國社會學(xué)知識資源,需要在差序格局與雙軌政治所指引的方向上作進一步的知識推進。循此在“賤籍”的身份社會發(fā)現(xiàn)平等訴求,在君主專制中彰顯天下為公。進而在現(xiàn)代政治的參照下,發(fā)現(xiàn)“儒學(xué)必須補課”的現(xiàn)代處境,一方面確立儒學(xué)在中國人生活中的持續(xù)性而又需要順應(yīng)而非抗拒現(xiàn)代的儒學(xué)研究大方向,另一方面則需要大力彌補儒學(xué)的科學(xué)與國際關(guān)系之缺。并從根本上矯正以血緣建構(gòu)現(xiàn)代社會的主張,確認對自由民主現(xiàn)代追求的確當(dāng)性。真假經(jīng)學(xué)因此截然分流。一個現(xiàn)代儒學(xué)研究的總體結(jié)論躍然紙上,“我們必須徹底清算‘王朝經(jīng)學(xué)’,才能救出并發(fā)展作為中華文明根與魂的真經(jīng)學(xué)”。這是一個很理智的結(jié)論。
作為一部具有理論雄心的儒學(xué)研究新著,總是會隨之拔高人們的期待心理。若暉這部著作,如引起相關(guān)討論,對儒學(xué)研究朝縱深處推進將不無益處。粗粗想來,可能引發(fā)人們討論或爭辯的地方,大概有這么幾個方面:一是若暉以對儒學(xué)的廣義社會學(xué)探討,排拒儒學(xué)的哲學(xué)論述,可能會引起已經(jīng)形成現(xiàn)代中國知識傳統(tǒng)的儒家哲學(xué)探究者的反詰。在舉起透視儒學(xué)與中國的方法透鏡時,若暉自己所確立的方法理念強度因此會受到同等強度的挑戰(zhàn)。如果說社會學(xué)知識資源的重要性在若暉的分析中得到充分呈現(xiàn)的話,那么,作為一種現(xiàn)代知識傳統(tǒng)的“中國哲學(xué)”被若暉拒斥得可能就有些過分了。在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哲學(xué)”確實可能明顯扭曲了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真實面目,但它恐怕是中國傳統(tǒng)統(tǒng)合性知識遭遇西方現(xiàn)代分科知識時必然出現(xiàn)的一種知識轉(zhuǎn)型。在前一段時間熱鬧的“中國哲學(xué)的合法性”爭辯中,這一點已經(jīng)為學(xué)界所揭示。就此而言,若暉重視傳統(tǒng)中國的“真實”展現(xiàn),可能遮蔽了他對現(xiàn)代中國“真實”的揭示。相應(yīng)地,書末對現(xiàn)代中國的期待,可能會被他的傳統(tǒng)中國刻畫所窒息。體現(xiàn)他的知識旨趣的社會學(xué)取向,可能會因為他太過看重社會學(xué)是社會事實的揭橥,因此隱含一種以傳統(tǒng)規(guī)范取消現(xiàn)代規(guī)范的危險性。在某種意義上講,由于中國社會學(xué)缺乏社會理論的有效建構(gòu),事實上愈來愈喪失掉為現(xiàn)代社會辯護的功能,陷于為傳統(tǒng)辯護的陷阱。中國社會學(xué)往往借助人類學(xué)的理念展開其“社會人類學(xué)”的混合研究,就證明兩個學(xué)科的整合性研究內(nèi)涵模糊掉傳統(tǒng)社會與現(xiàn)代社會界限的學(xué)術(shù)風(fēng)險。
二是若暉對“治出于二”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政治結(jié)構(gòu)的揭橥,確實展示了理想之治與實際治理的兩個面相。其旨在揭示儒學(xué)與中國互動機制的四重結(jié)構(gòu),也切實發(fā)揮出矯正單一維度儒學(xué)研究的弊端,且全方位展現(xiàn)儒學(xué)與中國總體狀態(tài)的作用。但這也會催生進一步討論的余地:就前者講,若暉有效地揭示了國家治理理想與現(xiàn)實的分離狀態(tài),以及由此造成的“家族盛則有德無治,君權(quán)盛則有治無德”的悖謬。但存在于儒學(xué)思想史上旨在維護國家治理理想的主張,并不就此失去它的獨特價值,志在張揚這一治理理想的發(fā)散性主張(以及由此引導(dǎo)出來的現(xiàn)代儒家哲學(xué))并不因此喪失其現(xiàn)代意義。循此可知,若暉的分析會讓他遭遇兩個尷尬的問題:一是致力揭示傳統(tǒng)的“真實中國”是不是就可以自然而然地通向現(xiàn)代的“真實中國”?二是揭示傳統(tǒng)中國遭遇的治理悖謬,是不是就避免了現(xiàn)代中國重蹈覆轍?顯然不存在這兩個自然導(dǎo)出的結(jié)果的可能性。也許,現(xiàn)代中國同樣會遭遇“治出于二”的窘迫。“治出于二”會是人類解決國家治理問題的一種存在性難題嗎?如果是,那么若暉揭示的傳統(tǒng)“治出于二”即便是進入現(xiàn)代,也同樣化解不了;如果不是,那么現(xiàn)代會以什么樣的“治出于一”化解傳統(tǒng)的“治出于二”的根本矛盾呢?進一步的難題是,現(xiàn)代理想化的“治出于一”帶給人類的深重災(zāi)難怎樣面對、如何避免?
三是若暉的一些方法設(shè)定與重大論斷存在深入辨析的必要。首先,若暉以儒學(xué)與中國的互動機制,揭示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思想與制度互動機制,諸篇章之間盡管各依主題而立,但互動的總體狀態(tài)似乎還有待呈現(xiàn)出來。換言之,“以儒學(xué)為方法”的總體方法與具體辨析方法,可能并不是同一個方法。因為若暉對“以儒學(xué)為方法”的方法儒學(xué)與對象儒學(xué)的比較性闡釋非常簡略,以至于人們無法干脆利落地把握它的確切含義。期待若暉后續(xù)的研究能對之做出精彩闡釋。其次,若暉對“中國哲學(xué)”的批評性處理,確實啟人思考。但相應(yīng)知識傳統(tǒng)為何確立起來的深厚理由,可能為他所輕視。這也許正是傳統(tǒng)儒學(xué)必須經(jīng)受現(xiàn)代分科知識重構(gòu)的處境所致?因此不是研究者可以規(guī)避與否定的儒學(xué)研究進路。尤其是在若暉對王朝經(jīng)學(xué)與新經(jīng)學(xué)嚴(yán)加分辨的情況下,分科儒學(xué)難道不是深化儒學(xué)研究,并激活儒學(xué)現(xiàn)代活力的一種必然取徑?!再次,若暉對傳統(tǒng)儒學(xué)通向現(xiàn)代中國的理路刻畫,因為主要支撐的章節(jié)是兩個發(fā)言和一篇論文,因此存在論述簡略之處。這不僅讓全書在結(jié)構(gòu)上顯得有些失衡,而且論述上讓人覺得淺嘗輒止、以主張取代論證,不足以在現(xiàn)代時段呈現(xiàn)“以儒學(xué)為方法”的豐富內(nèi)涵。
若暉這部著作出版在即,他給我先睹為快的機會,并囑我為之序。上面談了一些讀后感,權(quán)作為序。不當(dāng)之處,請若暉與讀者朋友們指正。
【后記】
我在哲學(xué)系從事教學(xué)科研,轉(zhuǎn)眼已經(jīng)近二十年了。同時由于山東大學(xué)王學(xué)典先生的開示,我也盡力從宏觀視角探討中國歷史。兩者相結(jié)合,使我日益認識到,近代以來以儒學(xué)為哲學(xué)的研究模式,存在著兩個根本性的弊端:既模糊了儒學(xué)的歷史面貌,又阻礙了哲學(xué)在中國真正生根。
近年來,我努力將自己的粗淺認識行諸文字,也獲得了一些師友的關(guān)注,贊同者有之,質(zhì)疑者也不乏其人,都是我的良師益友。
2024年4月20—21日,復(fù)旦大學(xué)歷史系經(jīng)學(xué)研究中心舉辦“經(jīng)典和時代:經(jīng)學(xué)研究的古與今”學(xué)術(shù)工作坊,承蒙鄧志峰(秉元)兄不棄,嚶鳴相召。與會者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張鈺翰兄,乃朱維錚先生高足,我們坐席相鄰,相談甚歡。承鈺翰兄抬愛,為其主持的經(jīng)學(xué)叢書約稿,余遂應(yīng)以“以儒學(xué)為方法”,正好借此契機,將歷年思考整合獻芹,以就教于當(dāng)世之君子。感謝鈺翰兄!
本書共收文16篇,其原始發(fā)表出處及與本書對應(yīng)章節(jié)如下:1. 緒論李若暉《儒學(xué):由對象到方法》,載《華中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2023年第1期,第8—13頁。
2. 第一章李若暉《論儒學(xué)的制度之維及中國哲學(xué)之成立》,載《孔子研究》2022年第3期,第5—28頁。
3. 第二章周丹丹、李若暉《歷史社會學(xué)視域中經(jīng)典概念及其研究范式之反思——以“差序格局”為中心》,載《史學(xué)月刊》2019年第2期,第95—115頁。
4. 第三章第一節(jié)周丹丹、李若暉《古代中國地方力量“自下而上”的運作:重論費孝通的雙軌政治》,載《復(fù)旦學(xué)報》2019年第3期,第101—110頁。
5. 第三章第二節(jié)周丹丹、李若暉《寓封建于郡縣:論費孝通“雙軌政治”的歷史真實》,載《史學(xué)月刊》2021年第4期,第98—106頁。
6. 第四章第一節(jié)周丹丹、李若暉《“倫”的語義與哲理》,載《周易研究》2024年第4期。
7. 第四章第二節(jié)李若暉《經(jīng)典詮釋視角下曾元對曾子孝論之調(diào)整》,載《中州學(xué)刊》2019年第7期,第101—104頁。
8. 第五章第一節(jié)李若暉《論正常之惡:郭店竹書〈魯穆公問子思〉的哲學(xué)分析》,載《國際儒學(xué)》2023年第1期,第99—102頁。
9. 第五章第二節(jié)李若暉《人何以能質(zhì)疑鬼神——上博竹書〈鬼神之明〉中的人之知》,載《哲學(xué)動態(tài)》2019年第12期,第53—57頁。
10. 第五章第三節(jié)李若暉《由經(jīng)學(xué)而哲學(xué):古公亶父避狄事之哲學(xué)分析》,載《江淮論壇》2024年第4期。
11. 第六章第一節(jié)周丹丹、李若暉《重返費孝通思想的歷史視野》,載《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6期,第28—34頁。
12. 第六章第二節(jié)李若暉《賤籍與身份社會》,載《光明日報》2016年8月1日第11版。
13. 第六章第三節(jié)李若暉《中國古代對于君主專制的批判》,載《文史哲》2016年第5期,第23—33頁。
14. 第七章第一節(jié)李若暉《儒學(xué)必須補課——在第二屆“生活儒學(xué)”全國學(xué)術(shù)研討會上的發(fā)言》,載《當(dāng)代儒學(xué)》(第16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8—60頁。
15. 第七章第二節(jié)李若暉《儒學(xué)與血緣——在“儒家自由觀念建構(gòu)”學(xué)術(shù)研討會上的發(fā)言》,載《當(dāng)代儒學(xué)》(第15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11—114頁。
16. 第七章第三節(jié)李若暉《“制度經(jīng)學(xué)”的終結(jié)——從皮錫瑞〈經(jīng)學(xué)歷史〉說起》,載《光明日報》2021年12月11日第11版。諸文收入本書時都進行了修訂,如蒙引用,請以本書為準(zhǔn)。
清華大學(xué)政治學(xué)系任劍濤先生多年來一直關(guān)心我的學(xué)術(shù)成長。小書承蒙任先生惠賜大序,令蓬蓽生輝,至為銘感。
感謝合作者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人文與發(fā)展學(xué)院周丹丹老師。感謝為拙文面世付出心血的師友們。
中國人民大學(xué)國學(xué)院鐘章銘、康杰、楊清瑞、廖馳灝、賈枝潤、張羽翩、左家齊諸同學(xué)幫助核實引文、校對清樣;賈枝潤同學(xué)編制了參考文獻,一并致謝。
大疫三年,幾位年高德劭的師長不幸先后辭世,倍感哀痛:武漢大學(xué)陶德麟老校長、山東大學(xué)吉常宏老先生、北京大學(xué)郭錫良老先生、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王葆玹老先生,以及武漢大學(xué)盧烈紅老師,永懷恩銘。
臺灣大學(xué)中文系夏長樸先生,有長者之風(fēng),素所敬仰。2018年8月28日,當(dāng)時我在廈門大學(xué)哲學(xué)系任教,曾致函懇請先生來廈講學(xué)。翌日即收到先生賜復(fù):“我同意明年春季或秋天訪問貴校一周,做二至三場演講。因時間尚早,不妨在年底或明年初再確定。您看如何?”但是當(dāng)我們初步商定來訪時間和日程時,卻發(fā)生意外,夏先生于2019年3月17日賜函:“我本已預(yù)定四月下旬或五月初赴貴校作二至三場系列演講,主題與各場次題目亦已確定,一俟來函即奉上,以便閣下作業(yè)安排。不巧的是,上周內(nèi)人不慎跌倒受傷,經(jīng)臺大醫(yī)生診斷,系老人退化性骨折,雖僥幸不必開刀,但傷勢不輕,按時服藥之外,必須暫停日常活動,徹底休養(yǎng)四至六個月,方能痊愈恢復(fù)正常。目前小兒遠在國外,家內(nèi)無人,所有內(nèi)外各事皆由我一人承擔(dān),暫時難以分身遠行。原本預(yù)定三月底赴美開會,已去信取消。此外,九月中我又將返回臺大開課一學(xué)期,學(xué)生來自各大學(xué),向?qū)W心切,授課時間短暫,亦不宜請假。經(jīng)再三考量,迫于無奈,只好將赴貴校演講一事延期,改為明年三月開學(xué)后。此一更動,勢必增添貴校作業(yè)麻煩,不知是否合適?煩祈便中示告,情非得已,先此致歉。”我立即回復(fù):“路途遠隔,于師母療傷不能有所助益,深感愧疚。惟愿師母早日康復(fù),至誠禱之。先生也請多多珍攝。期盼改日蒞廈賜教。”12月23日,夏先生賜函:“內(nèi)人傷勢經(jīng)長期療養(yǎng)后,目前已大致痊愈。醫(yī)囑只要不過勞,應(yīng)可恢復(fù)正常作息。經(jīng)考量后,我有意于明年二月底或三月初訪問貴校,約停留一周左右,做二至三次演講,以履行前約。此一建議如果合適,煩請便中示告,我就將演講題目及個人資料另函寄上,以便貴校辦理相關(guān)事宜。謹此奉告。也謝謝您的盛意。”我在半小時后回復(fù):“不知何故,明年預(yù)算編制迄未啟動。照往年經(jīng)驗,11月份開始編制下一年度預(yù)算,獲批要到第二年三四月份,經(jīng)費正式到賬約為五月。因此,只能待學(xué)校開始編制預(yù)算,生以先生講學(xué)事申報獲批之后,再請賜下相關(guān)資料,做正式講學(xué)申報。但時間應(yīng)該在明年開學(xué)之后了。”夏先生于當(dāng)日晚間賜復(fù):“謝謝您的迅快回復(fù)。我原訂二月底三月初訪問貴校,主要是今年返回臺大授課,學(xué)期結(jié)束過完年正好有空檔,三月中又另外有事,赴貴校演講一事答應(yīng)已久,想趕快履約,以免拖延太久。既然邀請程序需要相當(dāng)時間,此事就不急。等貴校申報手續(xù)完成后,煩請通知我,我再將題目及個人資料寄上,屆時再確定赴貴校演講的時間。依我估計,成行最快恐怕要到明年九月以后。明年我不必上課,時間比較寬裕。此事給您增添不少麻煩,實在是抱歉!在此再次致謝。”此事就這樣耽擱了下來。孰料2020年疫情突起,講學(xué)事自然不再可能。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疫情方熾,夏先生竟于2021年11月1日22時51分不幸辭世,天人永隔,從此再也無法親聆教誨了。今特抄錄往來郵件,以表遺憾,以志哀思。
李若暉
2024年8月7日